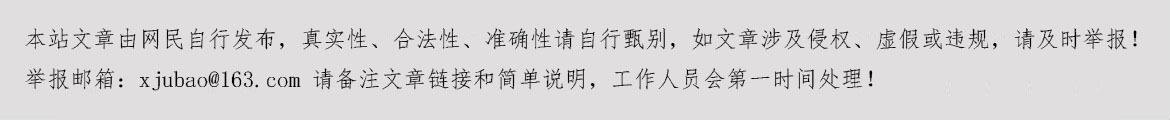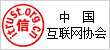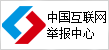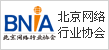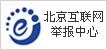女儿给亡父注销户口:对着证件照泣不成声,为何这事会触发共鸣?
2022-02-12 19:32:02
安徽滁州一女子在给亡父注销户口时,对着父亲的户籍照片泣不成声。虽然这事的“发生逻辑”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回到具体生命的觉解上,大概只有真正经历过生离死别后,才可能有超脱的可能性。
普遍而言在凡人一生的历程中,我们一般先失去祖父母,然后失去父母,再就是配偶、兄弟姊妹和朋友。这都是我们余生会承受的巨大痛苦,要避免这些痛苦,只有自己早死,可这又会令别人承受丧失亲朋之痛。
说到底,就好像关系链中的痛苦符合“守恒定律”,不是你痛苦,便是他(他)痛苦。在很大程度上,这既是人性的枷锁,又好像是人性的血脉。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不同的关系下,所呈现出的痛苦程度也是不同的。
以安徽滁州女子的“泣不成声”来讲,可能早在她父亲离世的时候就发生过很多次,只不过当“户口身份”概念上的父亲将永远被注销时,她便再次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得不承认在死亡的问题上,当事人永远是来不及审视,而亲朋们却会陷入长久的悲苦困境。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面对亲朋们死亡的事上,悲苦的底色里主要交织着两种难耐:其一、存在过的美好关系突然失去具体的勾连,难免会生出悲凉之感;其二、直面亲朋们的死亡,自然也会想到自己的死亡。
就“其一”来讲是最为容易看到的部分,因为人之常情已经说得很直白。而“其二”的存在却总是很隐蔽,多数时候都会掩藏的很深。以至于当父母的死亡来临时,我们也好像隐约看到自己的生命边际。
不过回到“女儿给亡父注销户口对着证件照泣不成声”的事上,也反映出一种朴素的生命存在观,也就是作为“肉身的人”即便会被死亡彻底摧毁,但与现实世界却还存在具体的勾连,起码在精神延续上,曾经存在就意味着永远存在。
当然就现实而言,“三代人”依然是生死勾连的主要界限。但凡超出“三代人”,死亡和现实就显得比较疏离,虽然代际延续过程中会有人讲述更久远的往事,但是就因为不曾发生过真实的互动,就会显得不那么真实,即便晚辈的骨血里沉积着长辈的秉性。
这使得人们总是对父母的祖父母的死亡没什么感伤,甚至有些人对于父母的父母的死亡也没那么感伤。说到底在情感的维系上,最为重要的还是现实的互动,而对于那些被编织出来的族谱,只是之于集体荣光叙事的存在,跟具体的情感没什么太大关系。
另外在面对亲朋死亡的事上,有的人一辈子难破悲苦底色,有的人几天后便可以走进新生。在这个问题上,以道德审视涉入,前者会被认为是有情有义,后者会被认为是人情薄凉;可要是以理性审视,前者反而显得不够清醒,后者反倒被认为是超脱的态度。
对于两种审视方式,到底趋向哪种好始终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作为具体的个人来讲,最好还是不要太过偏向一端。从某种层面上而言,悲苦的过程也是超脱的过程,就比如生者为死者操办葬礼,如果从实际意义出发,它只是在慰藉生者。
说到底对于死者的尊严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生者头上,毕竟人伦作为人与人之间亲疏远近的有意义关系以及由此自然发生的“物理性温情”(汉娜·阿伦特所强调的“挤在一起产生的温度”)总是值得回味的。
与此同时唐诺说:“死亡是休息、是大眠、是在广阔星空下舒舒服服躺下来,时间告终,不会有更糟糕更疲惫的事再发生”。我们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时刻心知它会到来,还知道这无可避免,但是弗罗斯特说:“入夜前我还有几里路要赶”。
所以回到安徽滁州女子的“泣不成声”上,对于她而言可能过好未来的生活,就是在实践弗罗斯特所言的“入夜前的赶路”,同时那也是她父亲最希望看到的图景。甚至从时空上追溯,她的父亲也曾有过类似的感受。
循此可以理解,类似中元节这类跟死亡挂钩的节日,除却仪式感中固有的鬼魅色彩,可能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在消解死亡的可怖感,也就是死亡并不是个体意义的终结,只要活着的时候有过美好呈现,那么就意味着死后依然能跟这个世界保持关联。